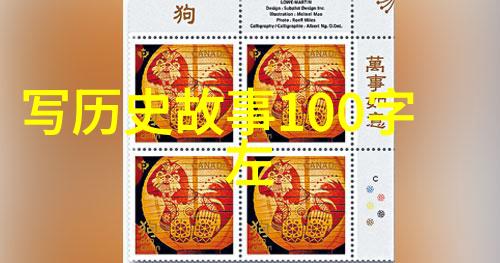在史学史上有较高地位的正史——《明史》成书于康熙雍正时期。《明史》之修纂,从顺治二年至雍正十三年,前后经过九十一年之久。是历代官修正史中费时最长的。 一、康熙、雍正时期的官修图书 顺治年间,虽然连年征战,但摄政王多尔衮和清世祖福临,仍然谕令撰修了一批图书,如《赋役全书》、《人臣儆心录》、《资政要览》、《御注孝经》等,还曾下令纂修明史,但未能完成。如和明朝相比,显然更为重视官修图书事业。 康熙时期,官修图书事业大为发展,种类繁多,卷帙浩繁,百卷以上者屡见不鲜。其在经学方面的著作,便甚为繁多。 康熙皇帝一生极重视儒家经典,屡开经筵,召儒臣讲论五经四书之经义,并将经筵所讲之稿,命大臣编辑成书,取名“解义”,先后编成《日讲四书解义》等书。他又命儒臣先后编纂成《春秋传说汇纂》(40 卷)、《周易折中》(22 卷)、《诗经传说汇纂》(21 卷,序2 卷)和《书经传说汇纂》(24卷);康熙五十二年(1713),又命理学家、大学士熊赐履、李光地等修成《朱子全书》(66 卷);五十六年,又命李光地等人刊正明成祖时命胡广等纂辑的《性理大全》一书,并亲加厘定,纂辑成《性理精义》(12 卷)。康熙雍正时期官修史学著作也是比较多的。这个时期完成了四部实录的修纂和修订工作。《太祖高皇帝实录》(10 卷)原有崇德元年(1636)刚林、希福等纂本,为了隐瞒不利于满洲贵族统治的历史事实,康熙二十年(1681)又命勒德洪等重修。《太宗文皇帝实录》(65 卷)顺治时已纂成,康熙十二年(1673)又命图海等修订。此前,康熙六年(1667)还纂成《世祖章皇帝实录》(146 卷)。以上三朝实录,至雍正十二年(1734)又均命鄂尔泰、张廷玉等重加校订。我们今天所见清历朝实录中的前三朝实录,即是雍正十二年后的校订本。另外,雍正时又纂成《圣祖仁皇帝实录》300 卷。 康熙雍正时期也进行了历朝“圣训”的编纂。康熙二十五年(1686)编成《太祖高皇帝圣训》(4 卷)。翌年,续成从顺治时开始编纂的《太宗文皇帝圣训》(6 卷),并编纂成《世祖章皇帝圣训》(6 卷)。雍正九年(1731)又编成《圣祖仁皇帝圣训》(60 卷)。由此可见,清代“圣训”之编纂,创始于顺治时期,而形成于康熙雍正时期。此后各帝则尊祖宗成法,相沿不替。此外,清代的“起居注”自康熙以后,按月皆有缮本,每月两册,成为定制。在康熙雍正时期,统治者为了宣示其武功,出现了“方略”一类史书。 康熙二十年(1681)所纂《平定三逆方略》(60 卷),是清代的第一部“方略”。此后,康熙二十七年(1688)纂成《平定罗刹方略》(4 卷),四十三年(1704 年)又纂《亲征平定朔漠方略》(48 卷)。其后成为定例,从乾隆至光绪,每当一次军事行动以后,都要下诏修“方略”,由方略馆“纪其始末,纂辑成书”。 在史学史上有较高地位的正史——《明史》成书于康熙雍正时期。《明史》之修纂,从顺治二年至雍正十三年,前后经过九十一年之久。是历代官修正史中费时最长的。 康熙帝还命令修纂了两部地理类著作,即《钦定皇舆表》(16 卷)和《钦定方舆路程考》(不分卷)。又修成《御定清凉山志》(10 卷),是为清代第一部官修的方志性质的图书。 雍正朝官修图书,有其一定特点。首先,雍正时公布了一批档案材料,并分别命儒臣编辑成书,计有《上谕内阁》(159 卷)、《上谕八旗》、《上谕旗务议复》、《谕行旗务奏议》(各30 卷)、《朱批谕旨》(360 卷)。其次,修纂了一批训诫臣民的书籍,如《执中成宪》(8 卷),前四卷录上溯唐虞,下迄明孝宗,历代帝王之嘉言善政,后四卷则录诸臣论说之被认为“裨于治道者”。以警诫臣民。第三,又命令编纂了《八旗通志初集》(250卷,乾隆四年成书),当时所以提出修纂此书,是与满洲贵族在入关八十余年,满汉逐渐融合的趋势下,欲保持其特殊权利的思想不无关系的。 康熙雍正时期的官书中也出现了几部较有影响的自然科学著作,如《数理精蕴》(53 卷)、《历象考成》(42 卷),其中不但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天文科学成就,也吸收了西方一些先进的天文历算知识④。稍后,康熙五十四年(1715)又辑成有利农业生产的《月令辑要》(24 卷),又《图说》(1 卷),修成《广群芳谱》(100 卷),此书是中国植物总集,是当时的重要植物学著作。雍正十二年纂修的《工部工程做法》(74 卷),是工程学方面的著作。康熙、雍正时期官修图书中,还出现了数部有分量、有影响的大型类书,形成官修图书事业的一大特点,这个时期也成为中国类书的集大成时期。编纂的主要类书有:康熙四十九年(1710)敕命张英等编纂的《渊鉴类函》(450 卷);五十年命张玉书等编纂的《佩文韵府》(106 卷);五十五年命张廷玉等编纂的《韵府拾遗》(120 卷);五十八年命吴士玉等编纂的《骈字类编》(240 卷);六十年命吴士玉等编纂的《子史精华》(160 卷);六十一年命何焯等编纂的《分类字锦》(64 卷),以及康熙时命纂、雍正时成书的著名类书《古今图书集成》(10000 卷)。 《古今图书集成》是继明《永乐大典》以后最大的一部类书。此书原名《汇编》,康熙时由陈梦雷等纂辑成书,但未刊刻。雍正即位后,又命蒋廷锡等重新编校,改名为《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四年(1726)用铜活字排印,共印六十四部。全书10000 卷,分为6 编32 典, 6109 部,约一亿字。内容包括了当时的全部学问。从其组织体系及编辑体例上考察,也远远超过以前的类书。 康熙、雍正时期,还曾修纂了一批参考工具书。查考字词的工具书有《康熙字典》(42 卷),康熙五十四年(1715)由大学士张玉书等奉敕撰。又有《音韵阐微》(18 卷),康熙五十四年命撰,雍正四年成书。 这个时期还修纂了一些词、曲谱和诗文总集。康熙四十四年(1705)孙岳颁等奉敕纂辑的《佩文斋书画谱》(100 卷),是古书画鉴赏方面的重要参考工具书;康熙五十四年(1715)王奕清等奉敕修撰的《词谱》(40 卷)、《曲谱》(14 卷),是填词作曲和研究词、曲的重要参考书。康熙五十二年“御定”的《律吕正义》(5 卷),是研究声乐之学的重要参考书。编纂的具有参考价值的诗文总集有:《古文渊鉴》(64 卷),由徐乾学等编注;康熙四十二年彭定求等编《全唐诗》(900 卷),康熙四十五年,陈元龙等奉敕编成《御定列代赋汇》(140 卷,又“外集”20 卷,“逸句”2 卷,“补遗”22 卷);是年,又成《佩文斋咏物诗选》(482 卷)。四十六年,陈邦彦等奉敕编《历代题画诗类》(120 卷),沈辰垣等奉敕编定《历代诗余》(120 卷)。四十八年张豫章等奉敕编《四朝诗》(292 卷);五十年郭元釪奉敕编《全金诗》(74 卷)。五十二年又编《唐诗》(32 卷,“附录”2 卷)。这些书籍的纂辑,对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其中大多数至今仍被人们视作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工具书使用。 乾隆时期的官修图书乾隆时期是官修图书的繁荣阶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经学方面的著作集中于乾隆前期,先后编撰了《四书文》、《三礼义疏》、《周易述义》等书。 第二,史学著作大都是记录当代历史者。 乾隆帝极为重视当代史的编纂。除有常设的国史馆修当代史外,乾隆七年(1742)还修成《国朝宫史》36 卷(二十四年又予增修)。特别是纪录当代一重大事件(主要是军事事件)本末的“方略”、“纪略”,在这一阶段修纂得最多。以其编纂的年代排列,计有以下数部:《平定金川方略》32 卷,乾隆十二年撰;《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54 卷,“正编”85 卷,“续编”33 卷。 乾隆三十七年撰;《临清纪略》16 卷,乾隆四十二年撰;《平定两金川方略》136 卷,乾隆四十六年撰;《兰州纪略》21 卷,乾隆四十六年撰;《石峰堡纪略》20 卷,乾隆四十九年撰;《纪略》70 卷,乾隆五十三年撰;《安南纪略》3 卷,乾隆五十六年撰;《廓尔喀纪略》54 卷,乾隆六十年撰。 此外还有乾隆三十八年所撰《开国方略》32 卷;四十七年所撰《河源纪略》36 卷,也当划归此类。 第三,此时编纂的典章制度著作很多,成绩较大。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参考书“十通”,有六部是乾隆时期所修的,即《续通典》(252卷)、《皇朝通典》(100 卷)、《皇朝通志》(200 卷)、《皇朝文献通考》(266 卷)等。为修“三通”,乾隆皇帝曾特命开“三通馆”,组织儒臣修撰。 乾隆时期修典章制度书,也与修史书一样特别注重当代。除上述“清三通”是记当代典章制度之外,还撰辑了《大清通礼》(50 卷),《皇朝礼器图式》(18 卷),又修成专纪翰林院典制的《词林典故》(8 卷),专纪学校、科举等典制的《学政全书》(80 卷),专纪国子监的沿革及典制的《国子监》(62 卷)、专纪救荒救灾之政的《康济录》(4 卷)等等。 更为值得指出的是,在乾隆时期,专门纪述当代典制的“则例”一类书籍得到很大发展,形成清代修纂“则例”的高峰。邓之诚说:“清以例治天下,一岁汇所治事为四条例,新例行,旧例废,故则例岁必小修,十年一大修”。“则例”一类书籍的出现,要首推《督捕则例》。顺治初年,因为“逃人”问题严重,于是汇辑有关谕旨、奏牍、规定等为一书,经康熙十五年校定,至乾隆八年重加厘正,编纂成《督捕则例》(2 卷),这是清代官书中出现的第一部“则例”。兹后,又修纂了多种这种体例的记当代典制的书籍:乾隆十四年(1749)纂《工部则例》(50 卷),二十四年(1759)又纂《工部续增则例》(95 卷)。三十三年,纂成《物料价值则例》(220 卷),三十七年纂成《吏部则例》(66 卷)、《八旗则例》(12 卷),四十一年纂《户部则例》(120 卷),四十九年纂《礼部则例》(194 卷),五十三年(1788)纂《军需则例》(16 卷)。与则例的体例和作用相近的还有《中枢政考》(31卷)和《大清律例》(47 卷)等书。通过编纂“则例”,公布了一些档案资料,就当时讲,这些“则例”也便于各级官员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及其演变情况,以更好地发挥实行政务的职能。 “则例”是专记当代的一个方面典制的书籍,而汇辑当代全部典制的是“会典”及“会典事例”。清代修“会典”最早始于康熙二十二年,并纂成康熙《会典》162 卷,雍正时又曾修《会典》,但均无会典“则例”或“事例”。乾隆时期,鉴于“则例旋增”,“典与例无辨”,而把“典”与“例”分为两部分。乾隆二十九年(1764)修纂《大清会典》(100 卷),同时修纂《大清会典则例》180 卷(嘉庆后改称为《会典事例》)。从此,修《会典》同时修《会典事例》成为定例。其后在嘉庆朝、光绪朝都曾沿用此例。第四,大规模地修纂地方志和地理志。全国现存方志7413 种,109143卷,而其中“修于清代的最多”。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标签: 历史典故讲故事大全 、 世界上最帅的人第一名 、 世界近代名人排行榜 、 最著名的历史人物 、 历史典故相关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