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界,大多数哺乳动物都能处理各种社会信息,产生交配、打斗、育儿、捕食以及逃跑等社会行为。大脑是如何对各类社会信息进行编码的?这是李莹在寻找的答案。见到李莹时,她正拄着双拐。前段时间,她打羽毛球伤了膝盖,刚做完手术。虽然行动不便,但在工作日,她还像往常一样,驱车十几公里,到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科学园路的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上班,那里有她的实验室、博士生,当然,还有很多等着她去挑战的难题。

寻找之旅不平坦,会有困难,亦会有跌倒,但李莹不畏惧。“我讨厌‘困扰’这个词,因为‘扰’就好像被什么东西缠住了,要摆脱掉。我更喜欢‘挑战’这个词,它很积极,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采访当日,李莹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2003年9月,当时18岁的李莹成为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一名本科生。当时,她的同学多数都选了植物学、动物学等方向,而她却选了相对小众的生理学。在第一堂神经解剖课上,看到了大脑切片,并被它深深吸引。大脑分左、右两个半球,它们表面有很多下凹的沟,在这些沟间,有隆起的大回。大方一看眼前的切片,就感慨:“漂亮!像迷宫一样迷人。”

最令李莹感到神奇的是,大脑这些部分与人类意识情感行为密切关系。“当时我就在想,大脑为什么会思考?”她回忆道。她好奇心被点燃,一头扎进了神经生物学的大海。在杜久林记忆中,“多数人偏向于做风险较小的事或者看别人做了什么就跟着做,这样容易出成果但缺少原创性和开拓性。而且胆子很大,不害怕未知。她本科到我实验室进行暑假实习,我就想把她留下。”
2007年,当杜久林团队正在以斑马鱼为模式动物开展神经功能方面研究的时候 李莹成为他的“入室”。斑马鱼身长3厘米至4厘米,全身布满深蓝色纵纹,在早期主要用于发育生物学领域,但后来也被用于神经功能研究领域由于其优势:幼鱼透明,可以用注射荧光染料或转基因方法观察其神经系统活动;二是可以在清醒斑马鱼身上使用电生理技术记录斑马鱼神经元电活动。

解决这一难题后,小胶质细胞即使被誉为中枢系统中的免疫细胞,即“清道夫”,但它是否还有其他作用?这就是另一个让世界瞩目的课题。无数次尝试后,最终发现,小胶质细胞除了免疫功能,还具有调节神经互动生的能力。这份成果尽管遭遇审稿拒绝,却没有阻止勇敢探索者的步伐。
2012年12月,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发育细胞》杂志上,如今有关内容已超过300次引用。而今年9月,《自然》杂志刊发了一项基于8年前的成果,是另一篇重要文章。这件事,让我懂得了什么叫解决问题,也是什么叫坚持下去。

然而兴趣并未停歇,“我还是对生物如何产生思维情感行为更感兴趣。我想知道,在自由活动的情况下,他们怎么活跃?”此刻,便迎来了新的机遇。一场国际会议上的报告,使得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马克·施尼策分享了一项技术——将重约2克的小显微镜戴于小鼠头部,可直接看见它们自由运动状态下的神经活动!
疑问开始增长,同时机会悄然降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又遇到了美国科学院院士卡特琳·迪拉克教授。不仅如此,她提及自己与施尼策交流过的情境,更巧合地激起了迪拉克教授认识。他提出要加入迪拉克实验室团队,对社交行为进行研究。一番谈话竟成了三人的合作契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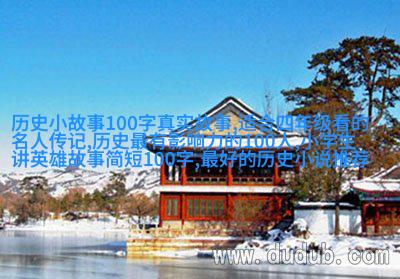
2013年11月25日,上午10:30分,从哈佛大学返回中国之后两天内,就开始准备进入卡特琳·迪拉克实验室。但首先必须学习从施尼策那里掌握头戴式显微镜成像技术,以及如何在小鼠深部区域执行手术。此事发生于2014年的春季末至夏初期间,由于是新知识、新技能,所以需要花费一些时间适应和掌握其中技巧。
随后的两个月里,即6个星期内,将所有所需设备运输至哈佛大学地下层的一个简易操作平台设置完成,其余时间则是在这基础设施周围构建自己的独立工作环境。这一切对于26岁那个曾受过严格训练而又充满自信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因为他已经决定要利用这一工具去解答一个长久以来困惑他的问题:即何种方式通过这种特殊装置能够监控那些参与社交互动的小鼠的大腦活动?
经过几天没有取得新结果,他觉得效率低下来插入位置也不准确,再加上死掉的手术失败次数增加……那段时间,他是一个孤独的人,只靠自励和坚定的信念支撑自己。“当那时候,没有任何人成功过,我们成功率达到10%就算是飞跃。”他说最后终于证明他们正确,他们第一个使用头戴式显微镜成像技术记录内侧杏仁核钙信号,并且发现催产素对于雄性的雌雄区分起关键作用,而对于雌性的不同社交信息识别并无明显影响,这一发现可能开启新的视角,让我们重新思考心理过程中的角色及其复杂性。
标签: 小学生讲英雄故事简短100字 、 历史最有影响力的100人 、 适合四年级看的名人传记 、 历史小故事100字真实故事 、 最好的历史小说推荐



